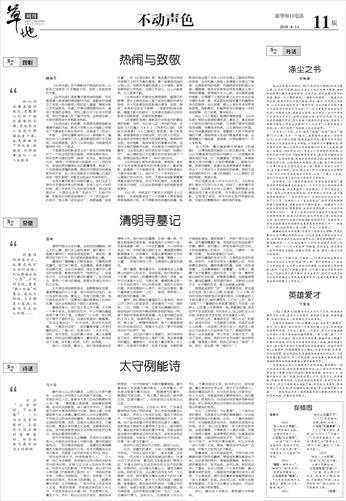
|
| 草地周刊 |
| 16 |
11/16 |
10
|
11
|
12
|
>
|
>| |
|
|
PDF版 |
 |
|
|
|
|
|
|
|
涤尘之书 |
|
|
|
| ( 2018-04-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
李咏瑾 诚如作者侯志明斯言,将《行走的达兰喀喇》定性为散文集,似乎并不准确。犹如赤子在天地之间睁开眼睛,他的叙述线索从最为亲近的母亲、父亲开始,依次延展到家中的老屋、提供一日三餐的粮仓、一掬清水的老井……随着成长的加速,视角中依次出现了母校、师长、妻子、不同的工作环境、以及非洲大陆等更为广袤的空间,而在不断行走的步履中又迎来孩子的成长与远行,下一代又重复开始这生生不息的人世探索之旅。读者这才惊觉,我们竟在一本书中陪伴了作者半生的岁月。这种从自我出发,依次见天地、见众生的直抒胸臆式写法,因为具备了高度的非虚构性,更像是一种最为接近文学表达本意的“个人口述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形式拓宽了传统散文表达的边界。
全书共15万字,分为“感恩”“感情”“感物”“感言”“感事”5个小辑,另加一个“篇外”,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作者参与“5·12汶川特大地震”抢险救援的历程。整本书的内容全部取材于作者真实的生活体验,从孩提时代的懵懂成长,再到离乡求学、踏上工作岗位后走南闯北的多年人生感悟,横亘了作者自1988年到2017年近三十年间的所思所想,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飞速发展紧密契合。侯志明在相关访谈中表示:“在写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要出版,我写的都是对我触动很大的,让我想起来或感动、或心酸、或不能忘记的人与事。那些存在首先是打动了我,使我必须把它记录下来,我才感到踏实。”由此,他记录了时代中真实生存的鲜明个体,而人与时代总是相互作用的。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也忠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
他写母亲,“女人固然是脆弱的,母亲却是坚强的”,瘦弱的母亲冒着酷暑在村里借了一个中午才为上学的他凑够一个月的口粮,然后再跋涉十多里路把二十多斤面送来了学校;他写儿时紧巴巴的生活,为辛劳的父亲买酒,被不慎跌碎的酒瓶划了一条长长的伤口,没想到这伤口让父亲心疼了几十年,“在他的心上一直没有愈合”;他写当年和新婚的妻子借居寒舍,那寒舍抬手可摸到屋顶,一抬腿就可以迈进房东家的菜地,屋寒情浓,这样的历历场景十八年后仍然让他难以忘怀……著名小说家刘庆邦在读后深为感动,“读志明写的母亲,我想到我母亲;读志明写的父亲,我想到我父亲;读志明回忆和妻子刚结婚时的困顿岁月,我眼前马上浮现出我和妻子刚结婚时住集体宿舍的那段日子……刚读了前几篇,我就情感上涌,双眼一次又一次湿润。”
随着叙述视角的延展,作者对人世的深切理解,更是扩展到生活中邂逅的苍茫众生,不仅有德高才硕的知名艺术家,还有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罗大众:摆买馄饨摊的小伙,擦皮鞋的匠人,以及他在煤矿工作时那些抹不去的人与事……他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勤谨,欣然落笔,洞见那些人性中的淳朴与超脱,流露出对真、善、美、爱等人道主义的永恒追求。
庄子曰:“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评价这些文章是“好读”的文章,“贵乎真情至上”,抓住了文学的本质: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渊源,而真情是文学的命脉。这种“口述史”式的散文探索,也引起了著名作家阿来的关注:“作者在自己跋中提到‘非专业写作’,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这种更接近文学表达本意的写作。这或许是更真切,更具生命本真意义上的表达。”

|
|
|
| 涤尘之书
|
|
|
|
|
|
| ( 2018-04-13 )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
|
|
|
|
|
|
|
涤尘之书 |
|
|
|
| ( 2018-04-1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 |
|
李咏瑾 诚如作者侯志明斯言,将《行走的达兰喀喇》定性为散文集,似乎并不准确。犹如赤子在天地之间睁开眼睛,他的叙述线索从最为亲近的母亲、父亲开始,依次延展到家中的老屋、提供一日三餐的粮仓、一掬清水的老井……随着成长的加速,视角中依次出现了母校、师长、妻子、不同的工作环境、以及非洲大陆等更为广袤的空间,而在不断行走的步履中又迎来孩子的成长与远行,下一代又重复开始这生生不息的人世探索之旅。读者这才惊觉,我们竟在一本书中陪伴了作者半生的岁月。这种从自我出发,依次见天地、见众生的直抒胸臆式写法,因为具备了高度的非虚构性,更像是一种最为接近文学表达本意的“个人口述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形式拓宽了传统散文表达的边界。
全书共15万字,分为“感恩”“感情”“感物”“感言”“感事”5个小辑,另加一个“篇外”,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作者参与“5·12汶川特大地震”抢险救援的历程。整本书的内容全部取材于作者真实的生活体验,从孩提时代的懵懂成长,再到离乡求学、踏上工作岗位后走南闯北的多年人生感悟,横亘了作者自1988年到2017年近三十年间的所思所想,正和我们这个时代的飞速发展紧密契合。侯志明在相关访谈中表示:“在写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要出版,我写的都是对我触动很大的,让我想起来或感动、或心酸、或不能忘记的人与事。那些存在首先是打动了我,使我必须把它记录下来,我才感到踏实。”由此,他记录了时代中真实生存的鲜明个体,而人与时代总是相互作用的。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也忠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
他写母亲,“女人固然是脆弱的,母亲却是坚强的”,瘦弱的母亲冒着酷暑在村里借了一个中午才为上学的他凑够一个月的口粮,然后再跋涉十多里路把二十多斤面送来了学校;他写儿时紧巴巴的生活,为辛劳的父亲买酒,被不慎跌碎的酒瓶划了一条长长的伤口,没想到这伤口让父亲心疼了几十年,“在他的心上一直没有愈合”;他写当年和新婚的妻子借居寒舍,那寒舍抬手可摸到屋顶,一抬腿就可以迈进房东家的菜地,屋寒情浓,这样的历历场景十八年后仍然让他难以忘怀……著名小说家刘庆邦在读后深为感动,“读志明写的母亲,我想到我母亲;读志明写的父亲,我想到我父亲;读志明回忆和妻子刚结婚时的困顿岁月,我眼前马上浮现出我和妻子刚结婚时住集体宿舍的那段日子……刚读了前几篇,我就情感上涌,双眼一次又一次湿润。”
随着叙述视角的延展,作者对人世的深切理解,更是扩展到生活中邂逅的苍茫众生,不仅有德高才硕的知名艺术家,还有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普罗大众:摆买馄饨摊的小伙,擦皮鞋的匠人,以及他在煤矿工作时那些抹不去的人与事……他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勤谨,欣然落笔,洞见那些人性中的淳朴与超脱,流露出对真、善、美、爱等人道主义的永恒追求。
庄子曰:“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评价这些文章是“好读”的文章,“贵乎真情至上”,抓住了文学的本质: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渊源,而真情是文学的命脉。这种“口述史”式的散文探索,也引起了著名作家阿来的关注:“作者在自己跋中提到‘非专业写作’,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这种更接近文学表达本意的写作。这或许是更真切,更具生命本真意义上的表达。”

|
|
|